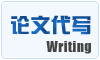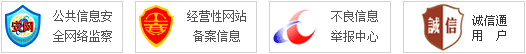|
115 动中的社会分工从大类上看也是粗糙的:工匠其实承担了建筑设计的脑力劳动和建筑施工的 体力劳动两方面的工作,难以拥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儒家文化背景之下的科举制度有“重 道轻器”的积弊, “君子不器”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其巨大惯性影响至今。李鸿 章曾尖锐地指出:“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 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2]。近代时期,第一代中国建筑师于欧、美 120 求学时,正值Beaux Arts 盛行,在观念上将建筑视为至高无尚的艺术,加之他们在社会角色 方面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之后继者,受“重道轻器”思想影响至深。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逃 脱这一怪圈:前中央大学时期,建筑学专业与建筑系设于工学院内,属工科,从理科角度看, 与“工匠”无异。于是理科学者们对杨廷宝先生这样的著名建筑师亦不以为然。可笑的是, 在建筑学科内部也形成了心照不宣的看法:建筑的艺术属性与(统治阶级专有的)权威性、 125 纪念性紧密相联,属“道”;而建筑的技术属性则更多与工程师、工匠和工艺关系密切,属 “器”。孰贵孰贱,一目了然。中央大学建筑系“由于艺术课居重要地位,又多半在艺术系 讲授,学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图案(笔者注:即建筑设计)课上,有重艺术、轻技术 的倾向。尽管在教学中工程技术课程内容繁多,但一直未被学生重视。因此自学校学习起, 就使学生滋生了‘大建筑主义’的思想倾向”[3]。1942 年的重庆大学建筑系甚至发生如此 130 “出格”之事:留德归来的系主任陈伯齐先生在教学上重视实际技术问题,而学生们则羡慕 邻校中央大学同学“画得好”,于是“将陈赶走,改换黄家骅任系主任,教学方式也仿照中 大”③。可见,观念的“重道轻器”导致专业的“重艺轻技”,这种认识通过第一代中国建 筑师开创的建筑教育传承了几代人,其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 建筑究竟是不是艺术?若将建筑与绘画、雕塑等经典艺术比较,其共同点在于都关注造 135 型,但建筑师如果不能提供一种基于建造——对于材料、结构、构造、施工、基地与环境诸 要素的综合权衡,即建筑自身所独有的生成逻辑与物质载体——的形式,其学科合法性就难 免受到质疑,其职业生存空间实际上也正在被“跨界”者蚕食。漠视表里关系的布景式做法 是从事绘画、雕塑、舞美、道具等艺术家们更为擅长的,要建筑师何用?“重艺轻技”的自 作多情和纠结于“儒匠之别”的枉费心机,其最要命处正在于主动放弃了学科自治的底线。 140 2.2 中观上的职业状况:建筑设计院=建筑画院? 当前,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基本状况与高等教育类似,专业分工极为细密。近代时期, 中国建筑师将前期策划(包括造价估算)、方案设计(包括方案构思、草图与正图绘制、效 果图制作)、施工图设计(包括室内装修设计)、工地咨询服务等角色集于一身,如第一代 中国建筑师杨廷宝、童寯等,甚至一些建筑师能身兼建筑、结构、设备等多专业工作。曾几 145 何时,前期策划成了“经济所”的专业,方案设计有了“创作所”(甚至“创作所”内还分 别设置了专管平面布局、立面造型、效果图制作的专项人员,流水线作业),施工图设计有 了“综合所”等等不一而足。不仅是不同的学科专业,即便是同一专业内部也进一步细分, 以至于出现了专做方案、施工图、效果图渲染与模型表现等新的、细密的专业分工。其设计 成果的生产组织模式是: 150 设计成果D=F(功能F1/空间S3+基地S1/场所G)+ F2(材料M/构造C1) + F3(结构S2)+ F4(设备BS) 其中,“创作所”只管F,高水平者或曰好事者最多涉及F2;而“综合所”则包揽F2、 F3 与F4,看来十分显要,偏偏“综合所”的使命似乎仅限于合成而与“创作”无关,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对于“创作”品质至关重要的F2 被扔给了材料商和承造商,图纸上的说法 155 是“详见厂家”,即: 设计成果D=F(功能F1/空间S3+基地S1/场所G)+ F3(结构S2)+ F4(设备BS)+“详见厂 家”。由于过分关注形式表象而忽视其与形式内核之间的关系,汶川震灾现场某倒塌教学楼 甚至连钢砼框架柱与相邻砌筑填充墙之间的“拉结筋”都取消了——为了追求立面凹凸有致 的视觉效果,相当一部分墙体位于框架外侧乃至悬臂梁上,这也无可厚非,关键是应采取的 160 构造措施却“忽略不计”,和对于“美”的处心集虑加以比照,令人深思:单纯视觉意义上 的“现代感”怎能替代整体意义上的“现代性”? 类似状况在吾国又何其之多!建筑设计院成为“建筑画院”,以及从业主体的“集体无 意识”,难道不也是对建筑教育的一种讽刺?在一个满足于表面文章的社会,追求效率和品 质,或者说“务实的建构”,似乎真成了奢望。 165 2.3 微观上的教育环境:“五七指示”与学校的尴尬 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影响下的建筑教育,在核心人力资源构成即教师的从业背景方面存在 明显缺憾:教师参与建筑活动尤其是设计实践的资源相对匮乏、涉足程度相对浅表,在与学 生的交流中缺乏足够的影响力与说服力。撇开高校设计力量难以与直接面对市场的“航空母 舰”型设计企业相匹敌这一因素不谈,即便是争取到了设计项目实施的机会,又有几人能够 170 坚持走完设计全过程?通常都被转移到所在高校的设计院接力完成,教师仅仅是方案设计师 而已。在高校考评体制(绩效考核)越来越看重“科研成果”的当下,这一倾向只会愈演愈 烈。而另一方面,择优聘请一线建筑师参与建筑教育也困难重重:在唯利是图的时代背景下, 一时还难以成批量涌现出甘愿受鞍马劳顿之苦、冒得不偿失之险的奉献型建筑师,著名建筑 师在设计课堂上打瞌睡也不是新鲜事。 175 教师尚且如此,学生的情况更为堪忧。因长期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学生连基本的生活 常识和生活技能都尚待补课,而专业层面的实践体验乃至于通过实践、观察来培养发现突破 口的问题意识,则更不必论及。有鉴于此,重庆市居然在大学生“六个一”社会实践活动中 重提“五七指示”的核心内容:学习工农兵。其提法和做法虽难免让人“心惊肉跳”,却也 反映了现行体制下当局者急于应对的迫切心情,以及照搬前辈的无奈[4]。 180 回顾历史,包豪斯的有关教育思想和实践自不必论,中国建筑教育模式也并非从一开始 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以中央大学建筑系为例,其课程表中的第4 学期“材料试 验(Materials Testing)”赫然在目,而其学术团队血缘之一的苏州工专建筑科,其课程表中 也有第1 学期的“金木工实习”[5]。又如清华大学营建系1946 年的课程草案中,也有“工 场实习”科目[6]。正是在1950 年代之后,这些关于建筑活动物质属性的课程从建筑学专业 185 的培养方案中逐渐消失了,若探究其中缘由,及其与“五七指示”的关系,应能咀嚼出别样 的深意。 3 建造教学在中国的开展状况及其前景 1980 年代后期以来,画图以外的制作和建造作为一种设计教学模式和工作方法,重新 引起了建筑教育界的兴趣。最先开始尝试的是一批老院系里的青年教师。进入新世纪以后, 190 建造教学实验在不同背景的院系内、不同课程体系中和不同因缘际会之下成规模地开展起来 ④。如果细分,不难看出各院系正在摸索一些不同的方向。 从材料类型看,是否采用真实材料与真实比例?应当说二者齐备的建造教学实验并不多 见,而南京大学(木结构)、香港中文大学(钢筋混凝土结构和木结构)、东南大学(竹结 构、钢结构和玻璃钢结构)的实验可视为代表; 195 从成果类型看,是建筑物还是构筑物?大部分建造教学试验选择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气 候边界的构筑物作为成果目标,换言之,对于建筑舒适度性能不作较高要求,仅提供可停歇 的空间覆盖,哪怕是透风漏雨;而东南大学2010 年度的“紧急建造”教学试验则试图对以 上状况作出调整:加入建筑物理环境性能作为考量因素,具有完整的建筑外壳和气候边界, 以此来推动学生对于建筑性能与设计限定之间关系的认知; 200 从技术支持的代际差异看,在建造设计中是否运用数字技术如生成设计、参数化设计与 数控建造技术?东南大学的“Angle X”和华南理工大学的一组实验作品堪称代表。传统意 义上的建造教学更多地强调前工业化时代(手工操作为主)和工业化时代(机器生产为主) 的建造技术,而后工业时代的信息技术和机器生产相结合产生了以自动化制造为核心目标的 数控建造技术——借助数控机床与机器人。此时,人的意义是否需要重新检讨?建筑师和工 205 匠究竟还能干什么? 从课程类型与体制关系来看,建造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设计教学模式,是否能进入 现行教学体制下的课程体系,从而实现体内循环?抑或成为师生自娱自乐的学术借口而游荡 于体制之外?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院系结合建筑设计课程(尤其是低年级建筑设计课程) 和建筑技术课程开展的建造教学实践,显然可以按既有课程本身的轨道顺利进入课表编排并 210 计算学分;而采用联合设计教学方式则比较复杂,进入课表算学分或未进入的都有具体案例。 这一点其实在现行考评体制下(教师工作量与绩效考核挂钩)非常重要:体制外操作偶尔为 之尚能不亦乐乎,但若总不能进入体制内将难以持续。至于纯属课外活动的建造设计实践, 因其完全与学校的教学体制脱开,本不应在此讨论,但正如李岳岩先生指出的那样:体制外 的活动反映出体制本身的问题,有助于促进建造教学乃至于建筑教育的反思和改进。这类活 215 动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由“香港无止桥慈善基金会”推出的“无止桥”计划,香港与内地多 原创学术论文网Tag:建筑论文代写 建筑论文发表 |